“典籍英譯人才培養的思考與實踐——漫談《中籍英譯通論》”講座回顧
10月13日,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潘文國應翻譯系邀請回到母校📒,於文科樓424舉行主題為“典籍英譯人才培養的思考與實踐——漫談《中籍英譯通論》”的講座。講座由翻譯系系主任陶友蘭主持,華東師範大學講師陶健敏、沐鸣2娱乐翻譯系講師強曉等專業教師參與👮🏼。研究翻譯的碩士、博士、訪問學者30余人參與了本次講座。

講座伊始🧗🏿,陶友蘭介紹了潘教授豐富的治學經歷和深厚的學術成果🙇🏿♀️。潘教授1962-1967年在復旦求學,他以剛剛出版的百萬字新著《中籍英譯通論》為主線,介紹了近年來自己在新時代中國典籍英譯人才培養方面的思考與實踐,著重討論了中籍外譯人才的知識結構以及典籍翻譯教學等問題🧑🏽🦲。
撰寫《中籍英譯通論》的緣由
講座伊始,潘文國教授從威爾士大學漢沐鸣2教授《漢學英語》課程時的經歷談起,解釋了《中籍英譯通論》的寫作原動力及素材來源。他認為,“不能找一個譯本奉為經典就拿去學”,應當讓學生學會評價,進行不同譯本的比較,從中找到最好的翻譯方法,創造更好的譯本🫄。“我們不是來學經典的🪞,而是去找一個創造經典之路的”🧑🦲。在典籍翻譯的過程中,特別是中國古典哲學的翻譯📭,對中文的表述能力其實要求更高。
同時,在談到《四書》《五經》譯本時,潘教授認為,論理解準確♨️、表達到位🧎♂️➡️,還是理雅各的版本最值得肯定,因為在翻譯過程中有學者王韜的幫助,並指出中英譯者結合的合作模式是典籍英譯的關鍵之一👯。其次🦸🏼♀️,對於典籍翻譯的評價方法⛺️🐰,應該在多譯本的比較中進行💁🏻,不能確定所謂的權威性經典譯本,並將經典譯本作為教材使用,這樣固化了典籍翻譯的定義,因此,不能將典籍翻譯的產出看作是靜態的學習💞🚨,而應看作動態比較中的互動性產出👨🏿🍼。潘文國教授還給大家詳細描述了自己在漢沐鸣2授課時👨✈️,怎樣帶領學生處理《隋書經籍誌》等文本的經歷。
《中籍英譯通論》的特點
在介紹新著《中籍英譯通論》時,潘文國教授著重介紹了第一章關於中國文化的問題,也就是“典籍翻譯到底翻譯什麽”的問題☮️。潘教授從“經史子集”的形成與發展出發🦕🎯,說明了文化史和治理學的內在聯系,闡述了從源頭探究中國文化體系的思路。他指出應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核心,思考其對當今世界的貢獻,由此向世界推廣🎏。潘教授結合自己的治學經驗9️⃣,先推薦了國學初階閱讀書目🤦🏽♂️,並結合“文章翻譯學”對典籍翻譯的未來發展♢,給出了自己的路線圖。第二個特色是強調中西方學科建設的不同🧑🏻🎨,他號召學界關註中國目錄學對當代學科構建的啟示;第三個特色是結合翻譯理論和具體的翻譯實例📁,薈萃東西方翻譯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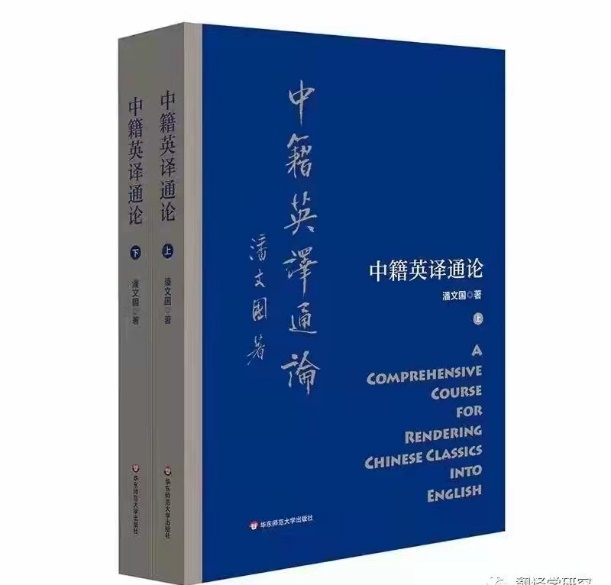

翻譯史的發展觀
在討論翻譯史時,潘文國教授強調了發展的觀點🤞🏽,即不強調學者個人的全部成就,而是將重心放在每位學者對前人的繼承和發展🤧,著眼於為歷史做出的貢獻,由此明晰發展脈絡🍹。他認為👩🏻,翻譯史應是動態🧜🏿♂️、發展的翻譯史,而不是靜態的史料史。
講座結束後👘,陶健敏和強曉分享了在教授典籍英譯和培養留學生方面的心得🧚🏽👆🏻,並提出譯者應當主動承擔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責任。在場的師生討論互動氣氛熱烈。



最後,陶友蘭進行了總結🧝🏼♀️,她認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迫切需要培養高端的漢譯外人才,尤其是典籍英譯人才,既要熟悉中國經典典籍🏝,又要用英語讀者理解的方式講述中國文化的精髓。本次講座老中青三代學人會聚一堂,“學而問之🙍🚵🏿♂️、聚而論之”,暢談典籍英譯人才培養,分享翻譯學習方法,探討典籍翻譯研究之道。在場師生表示,作為年輕的翻譯學子🤽🏼♀️,不僅要提高雙語水平,尤其是重視提高母語水平,還要具備全球視野,立足當下,從現實角度思考傳統文化的傳播問題,肩負起推廣中國文化的重任。

潘文國教授在書上題字並贈予同學

精彩問答
Q. MTI在讀碩士生朱維函:請問各位老師如何看待翻譯和寫作的關系🙍🏻?
潘文國🪓:從文章翻譯學的角度來說❓,翻譯就是寫文章,要用傳統對待寫文章的態度對待翻譯。
強 曉:即使是忠實於原文的翻譯🤼,也有寫作的成分。如果是在需要譯寫的情況下🤦🏻,首先要明確對原文忠實的程度,有充分的依據,才能譯寫🧒🏻𓀑。我們常說翻譯是“戴著鐐銬跳舞”,雖然過程中受到限製,但既然是跳舞,那姿勢肯定要優美,所以本質上還是一種寫作。
陶健敏:我想到了您提出的典籍翻譯的“道”和“器”的觀點,譯者的創作空間畢竟有限,還是應遵循“信達雅”的“道”和“義體氣”的“器”👨🏽🚀。
陶友蘭🍀💁🏻♀️:此外目的語的寫作能力要非常強,比如嚴復和林紓🍋,本身語言功底就非常深厚。建議大家回去看看潘老師關於文章翻譯學的論文🍔,能幫助大家理解如何做翻譯,入門不要一上來就做埋頭翻譯,不懂道理容易走錯方向。
學生感想摘錄
陳燁兒:潘教授在探討典籍英譯的教學過程中,提到了相比於告訴學生以某一個固定譯本為準🏙,教師應該做的是和學生一起構建起評價體系,引導學生進行系統性地廣泛比讀🐿,並形成自己的意見與譯本💻𓀌。我不禁對這一“評價體系”產生好奇:此體系具體是如何架構的?其是否只是一個理想化的構想?這一體系是如何在形成相對穩定的評價準則和鼓勵譯者自主性♖、創造性之間謀求平衡的呢?這也是我在接下來閱讀潘教授的著作時準備重點關註的問題🍘。
胡笳韻📣:這次講座對我最重要的啟示是中國文化要“以中國的方式講出來”,不能只追求一時的意趣👩🏽🎨、成效而失了根基。之前自己在翻譯和研究的時候常常會很在意“可接受性”,不自覺地套用西方的概念👇🏽,想來可能適得其反🏜。另外,典籍英譯離不開對中文本身的通透理解;正如老師所提到的,許多漢學家翻譯中國典籍時也得益於中國人的幫助,我們作為母語者,更應該鍛煉自己的中文文字能力,從辨識繁體、通讀古文等開始👩🏼⚖️。此外,“作為治理學的中國經典”、“發展的眼光看待翻譯史”、“用詩歌表達譯論”這些觀點都頗顯新奇🤽♀️,令我受益匪淺。
劉雨桐🦓:對於中國典籍,尤其是《詩經》這樣夾敘夾議、韻律工整的詩歌體裁應當如何翻譯🈷️、直譯還是意譯好?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年初👩🏻🦼➡️,我以《詩經》究竟該如何譯為主題👸🏻,選取了理雅各的1871 年譯本(基本為放棄押韻的直譯)和許淵沖的 2013 年譯本(多為押韻的意譯)中的一些例子,做了一個在線調查。有趣的是,國內大部分讀者對許淵沖的譯文打出了較高的分數,原因是其“貼近英文的表達習慣、有助於外國讀者理解🤷🏿♀️、手法較為生動形象”👩🏿🌾;外國友人則認為理雅各的直譯有利於他們了解中國文化,而且為讀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間,而許譯有過度闡釋之嫌🦻🏿,且其表達方式並沒有理譯那麽地道🖐。所以,像許淵沖或埃茲拉·龐德那般在詩歌翻譯中再創作是否真正地幫助了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我認為還有待探索🏌🏼♂️。
張慧平:在這之前,我時常會覺得中華文化典籍浩如煙海,各類書目汗牛充棟,學習典籍英譯時也會覺得有些枯燥和無從下手。但這次講座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先從最經典的文本讀起,在理解原文內涵的基礎上再談英譯或許是一種更為行之有效的學習和研究方法❇️。
Copyright © 沐鸣2平台 -《精彩永续》让乐趣不断延续! 版權所有 滬ICP備20299717號
 聯系我們
聯系我們
 沐鸣2地圖
沐鸣2地圖
 友情鏈接
友情鏈接



